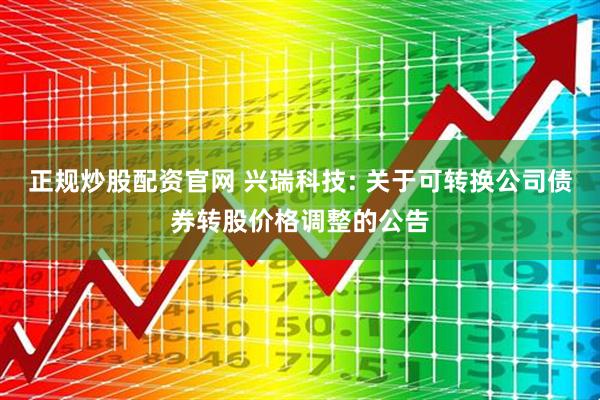一九三六年十月配资在线论坛,黄河以西。
一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队伍,在甘肃靖远附近分批西渡黄河。

他们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,许多人的脚上只有草鞋。
身后,是刚刚结束长征、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主力红军和殷切的期望;身前,是一条奉命要打通的、通往苏联的“国际路线”,以及一片完全陌生的、被地方军阀牢牢控制的土地——河西走廊。
他们最初被称为“西路军”。很快,他们将被称为“孤军”。
十一月十五日,甘肃古浪。
这是西路军渡过黄河后第一场硬仗。
对手是马步芳的精锐骑兵部队,被称为“马家军”。
这些人马术娴熟,枪法精准,作风凶悍,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。
西路军先头部队红九军,在古浪城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三日。
城墙是土夯的,挡不住重炮。
马家军的骑兵像黑色的潮水,卷着黄沙,一波一波地冲过来。
他们不用复杂的战术,就是冲锋,不断地冲锋,用马刀和血肉消耗你。
红九军将士,很多是参加过鄂豫皖、川陕苏区血战的老兵,经验丰富,意志如钢。
但他们从未在如此开阔的戈壁滩上,面对如此规模的骑兵集群冲锋。
子弹打光了,就用大刀、刺刀、枪托,甚至石头。
一个叫刘俊英的营长,肠子被打了出来,他塞回去,用腰带勒紧,继续指挥,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古浪城最终失守了。
红九军伤亡超过两千四百人,兵力折损三分之一,军参谋长陈伯稚、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、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高级指挥员牺牲。
这不是一场战役的胜负,而是一个预兆:在这条走廊上,战斗的残酷规则,与你所熟悉的任何地方都不同。
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,甘肃高台。
红五军军长董振堂,一位宁都起义的领导者,一位以稳健和忠诚著称的将领,率领三千余人进驻了这座小城。
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军,掩护主力。
很快,两万多马家军将高台围得铁桶一般。
没有援军。电台被打坏,与总部的联系彻底中断。
高台成了一座血色的孤岛。
战斗从城墙打到巷口,从巷口打到屋内。
子弹没了,就用刀;刀砍卷了,就用拳、用牙。
女战士、炊事员、伤员,所有人都拿起了能战斗的一切。
军政委杨克明在带领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。
一月二十日,城破。
董振堂带着少数警卫员退守到一座荒废的土楼上。
最后时刻,他把随身携带的怀表、钢笔和一枚苏维埃银元交给身边的战士,说:“这些,将来或许还能为革命起一点作用。”
随后,他举着手枪,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,从三丈多高的城墙上纵身一跃。
马家军割下了他的头颅,先是在高台城门示众,后来又被送到西宁,拍了照片,大肆宣扬“战果”。
董振堂的头颅至今没有找到,他的身躯,永远留在了高台那片被血浸透的黄土里。
高台陷落,红五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。
这是西路军最为惨痛的损失。
一九三七年二月,甘肃临泽倪家营子。
此时的西路军,已从远征军变成了一支疲惫不堪的求生队伍。
他们收缩在倪家营子一带四十三个屯庄里,试图建立临时根据地。
但这里不是陕北,没有群众的深厚根基,只有无尽的荒滩和冷酷的敌人。
最大的敌人,不再是马家军的骑兵,而是饥饿和寒冷。
河西走廊的二月,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。
没有棉衣,许多战士把能找到的所有布料——毯子、麻袋、甚至庙里的破幡——都裹在身上。
脚上的冻疮溃烂流脓,和破草鞋冻在一起,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
粮食早就断了。战马杀了,牲口杀了,最后,连皮带、皮鞋都煮了吃。
盐水煮麦粒,是唯一能进嘴的东西。
饿极了,有人扒开雪地,寻找一切可以咀嚼的草根。
伤病员没有药,伤口化脓生蛆,只能用盐水擦洗,那惨叫能撕裂人的灵魂。
马家军不急于总攻,他们像狼群一样,围着这片屯庄,日夜不停地骚扰、袭击、消耗。
西路军战士每天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提着枪进入阵地,击退一次或数次冲锋。
夜里,要在寒风中放哨,防止敌人偷袭。
睡觉?那是奢望。
很多战士,是在端着枪的姿势下,被冻僵,再也醒不过来。
倪家营子不是一场战斗,而是一场持续四十多天的、缓慢的凌迟。
每一天,都在流血;每一天,都在减员;每一天,希望都比前一天更渺茫。
三月十四日,甘肃肃南石窝山。
西路军最后的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。
能战斗的人员已不足三千。
会议决定:主要领导人陈昌浩、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;剩余部队分散游击,尽力保存火种。
石窝分兵,是战略的终结,却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的开始。
李先念、李卓然等人率领一支约一千五百人的左支队,向着祁连山深处挺进。
祁连山,海拔四千米以上,终年积雪,鸟兽罕至。
他们衣衫褴褛,弹尽粮绝,走进了这座“死亡之山”。
寒冷是主宰。
夜里,大家挤在石崖下或雪窝里,靠体温相互取暖。
第二天早上,总会发现身边有人再也叫不醒。
一个叫周纯麟的干部后来回忆,他们曾找到一个羊圈,在里面发现一点羊粪,就像找到宝贝一样,把羊粪揣在怀里取暖。
没有食物。雪,是唯一的水源和“食物”。
饿到极致,炊事员把最后一点牛皮烟袋剪碎,放在唯一的铜盆里煮,那点浑浊的汤,大家轮流喝一口。
后来,连前面部队留下的马蹄印里冻住的马粪,都被捡出来,看看有没有未消化的粮渣。
追兵依然在搜山。伤病员必须安置。
很多重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,恳求甚至用命令的口吻让战友把自己留下,塞给战友一颗手榴弹,不是用于杀敌,而是用于自己最后的尊严。
这支左支队,像一把被撒入雪山的盐,在极端的自然和人为的绝境中,一点点融化、消失。
最终,当李先念带领仅存的四百二十余人,历时四十三天,走出祁连山,抵达新疆星星峡时,他们个个形同鬼魅,骨瘦如柴,但眼神里,有一种从地狱归来的、冰冷的火焰。
更多的人,没有走进祁连山,或者没能走出来。
数千名西路军战士在战斗中被俘。
等待他们的,是比战死更为屈辱和残酷的命运。
马步芳将他们视为炫耀武功的战利品和可奴役的牲口。
大量被俘红军被残忍杀害,其中手段之酷烈,骇人听闻。
幸存者被编入“补充团”,做苦役,修公路、建营房,动辄遭受毒打和虐杀。
许多女战士的遭遇尤为悲惨。
她们被强行分配给马家军官兵做妻妾,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。
有些人被迫改姓埋名,在漫长的岁月里咀嚼着孤独和恐惧,像隐入尘沙的砾石。
还有大量失散人员,流落在河西走廊乃至青海各地。
他们躲过追杀,隐姓埋名,给地主放羊、扛活,在社会的最后层挣扎求生。
他们与组织失去了联系,有的甚至终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他们背负着失败者的沉重枷锁,在历史的夹缝中默默生存、老去、消亡。
西路军的结局,不是一个句号,而是一串漫长而痛苦的省略号。
它的“失败”,不是一个战略分析的结论,而是由高台的城墙土、倪家营子的冻土、祁连山的雪、被俘者的血、流散者的泪,共同混合浇筑而成的一块沉重的碑。
今天,当我们摊开地图,轻松地划过那条叫“河西走廊”的地理通道时,是否还能感受到一九三六年冬天沁入那土地的体温与铁锈味?
西路军的故事,之所以成为一曲挥之不去的“悲歌”,正是因为它拒绝被“虽败犹荣”的简单赞歌所收编。
它过于具体,具体到每一处伤口的形状、每一次饥饿的绞痛、每一个被放弃的名字。
它暴露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、误判、极限环境的碾压,以及理想在现实岩壁上撞出的淋漓鲜血。
铭记这曲悲歌,不是要清算旧账配资在线论坛,而是要对抗遗忘。
佳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